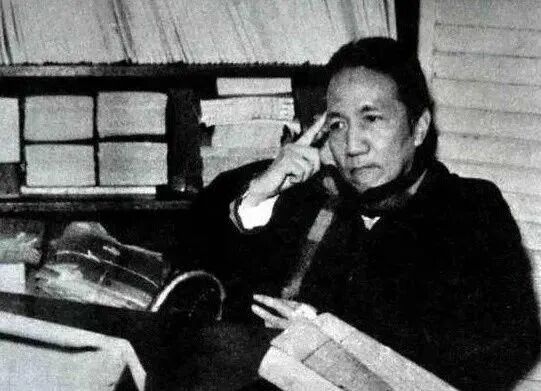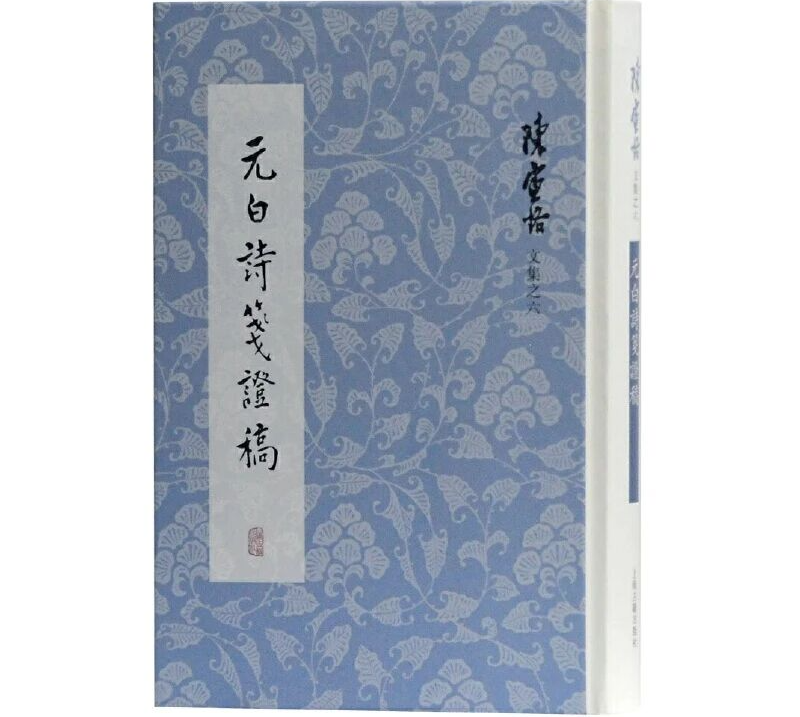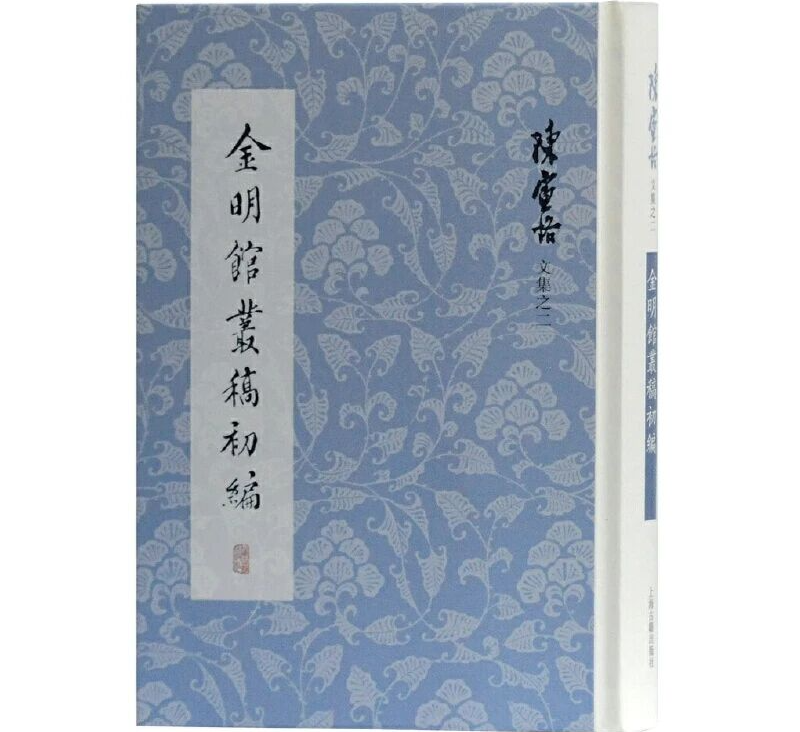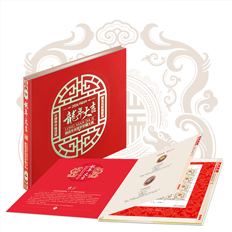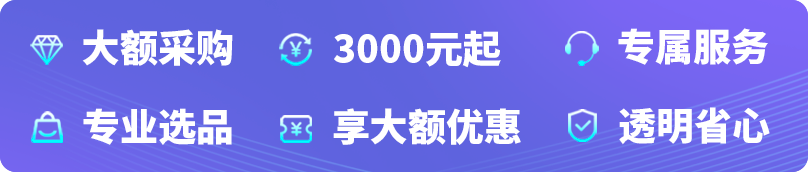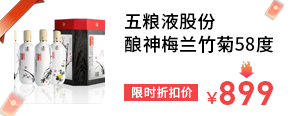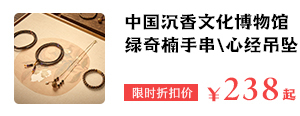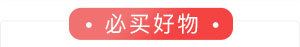刘梦溪|陈寅恪的文体论


独家抢先看
陈寅恪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其在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的学术创获,已为人们所习知。但他的治学特点,既出文入史,又熔史入文,其对辞章之学的看重和讲究,人们谈论得很少,甚至略而不及。其实,寅恪先生不仅是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慎思明辨的文论家,其文章观念和文论主张,置诸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坛,亦可谓独树一帜。
可以说,寅恪先生比任何现代学者都更重视对文体的研究,如同他创立了独特的阐释学一样,在他几十年的著述当中,也包含有相当系统的关于文体学的创辟胜解。
陈寅恪
古文运动和唐代小说
陈著《元白诗笺证稿》疏解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宗明义就提出,要正确理解这篇作品,一定要知道当时与之有关的文体问题。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寅恪先生援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的一段记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页)在作此引录之后,寅恪先生接着写道:
赵氏所述唐代科举士子风习,似与此诗(指《长恨歌》——笔者)绝无关涉。然一考当日史实,则不能不于此注意。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同上,第2页)
《元白诗笺证稿》
谁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萧颖士、李华、颜真卿、元结、独孤及、柳冕、梁肃、权德舆、李观、李翱、皇甫湜、韩愈、柳宗元,以及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都在唐代古文运动推动者的行列。但最主要的堪称领袖人物的则是韩愈。
寅恪先生强调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同时也是当时最佳小说的作者,这一判断涉及到唐代文体革新的大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说来确也令人感到诧异——提倡“文以载道”而又以承传正统儒宗自居的韩愈,竟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大感兴趣,不仅从文体的角度为之辩护,自己还动手进行创作,写出《石鼎联句诗序》及《毛颖传》等作品,难怪张籍要攻讦他“尚驳杂无实之说”,“有以累于令德”(张籍:《上韩昌黎书》,《韩愈资料汇编》第一册,1983年版,第9页)。裴度《寄李翱书》也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裴度:《寄李翱书》,《韩愈资料汇编》第一册,1983年版,第5页)《旧唐书·韩愈传》则说昌黎“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三册,第4204页)。对这类指陈,韩愈殊不以为意,只回答说他是“为戏耳”,连孔子都“有所戏”,他戏谑一番有何不可(韩愈:《答张籍书》及《重答张籍书》,《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62、164页)。何况于道并没有什么损害。实际上是当时的文士们对韩愈的革新文体不习惯,用旧眼光来看待新事物。
1936年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文章,专门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指出:“裴度所谓‘以文为戏’,与夫《旧唐书》之所指陈,皆学人基于传统雅正之文体,以评论韩愈者。在当时社会中,此非正统而甚流行之文体——小说始终存在之事实,彼辈固忽视之也。”(该文1947年由程千帆先生译成中文,金克木先生校正,收入1984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程著《闲堂文薮》,见该书第20至23页)充分肯定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以古文试作小说所取得的成功。不止韩愈,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也是小说体的文章,与当时已趋腐化之骈文及公式化之散文判若天壤。寅恪先生于此点进一步分析说:
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宜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致为张籍所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4页)
又说
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同上,第4页)
所以寅恪先生的结论是,唐代之贞元及元和时期,既是古文的黄金时代,也是小说的黄金时代。韩愈的贡献,是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来改进民间流行的小说,创造一种融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文备众体的“甚合实际之文体”,名曰复古,实则通今。
“以文为诗”和“以小说为文”
至于韩愈的“以文为诗”,历来有不同评价。要为两派:一派主张严文体分野,因此持否定态度,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韩愈资料汇编》第一册,1983年版,第168页)黄庭坚则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另一派以欧阳修为代表,对韩诗韩文并加推崇,在《六一诗话》中写道:“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故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欧阳修:《六一诗话》,《韩愈资料汇编》第一册,1983年版,第111页)两派对韩诗的评价迥然不同。
寅恪先生站在探讨文体演变和支持文体革新的立场上,对韩愈的以文为诗不仅正面给予肯定,而且评价甚高。他将此一问题和佛经翻译的文体联系起来,盖佛经原本兼备“长行”,即由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组成,但早期翻译者大都“改诗为文”,而并未取得“以文为诗”的成功。马鸣菩萨撰写的《佛所行赞》,是第一等的梵文佛教文学,但经过寅恪先生和钢和泰对汉、藏译文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译似尚逊于藏译”。因此他在深以为憾的同时写道:
退之虽不译经偈,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95页)
实际上唐诗向宋诗转变,韩愈有不可淹没的历史功绩。苏轼、黄庭坚诸人尽管对韩诗不无微词,但其所受韩诗的影响亦历历可见。所以赵瓯北才有“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195页)的说法。其实,文体的变化,常常是其他文体侵入衍变的结果。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写道: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各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圣集》卷八《诗赋》曰:“知非诗诗,未为奇奇。”赵闲闲《滏水集》卷十九《与李孟英书》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盖皆深有识于文章演变之原,而世人忽焉。(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0页)
读了锺书先生的论述,不仅于韩愈的以文为诗及以小说为文,可以得出正确看法,对寅恪先生的着眼于变化的文体论,也可以通解矣。盖陈、钱皆学问大家,他们对文体所持的立场不约而同,都是文体革新派的立场。
元稹和白居易的“新兴文体”
现在我们再回到对《长恨歌》的评价。寅恪先生所以从“当时文体之关系”的角度来析论《长恨歌》,是因为在他看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撰写的《长恨歌传》“本属一体”,此与元稹的《莺莺传》和李绅撰写的《莺莺传歌》乃为“一体”一样,两者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页)。实际上也就是唐代的贞元、元和之间,文坛上流行的一种新兴文体。这种新兴文体,按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的说法,是“史才、诗笔、议论”的综合,以“文备众体”为特征。寅恪先生显然对“史才、诗笔、议论”融为一体的历史写作方式极感兴趣,或者说他自己的史著之中就带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即使是论白居易的《长恨歌》,也要和陈鸿的《长恨歌传》联系起来,并连带为说,提出:“诗笔”指韵文而言,“白氏之歌当之”,“史才”和“议论”部分,“陈氏之传当之”。然后得一结论曰:“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同上)元稹的《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读者最感可厌,也不理解作者出于什么考虑一定要这样写。寅恪先生对此有新的解释,认为是文体特征的需要:“小说之文宜备众体。”
又《莺莺传》中有一段“张生”的“议论”写道:“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就是元稹为自己的“始乱终弃”的行为辩解的所谓“忍情说”,研究元、白的学者,大都视其为《莺莺传》的作者立身行事的癍污。但寅恪先生从论文体的角度着眼,关注的是此一“忍情说”正是元和新文体的“议论”部分,而其中莺莺等人的诗作则是所谓“诗笔”,所叙述的离合悲欢的故事,即所谓“史才”(同上,第116页)。这些都是当日“备众体”的小说不能不具备的条件。本来白居易曾说元稹的文章有“理周辞繁”的毛病,但寅恪先生认为,元氏文繁之病如果用来作小说,恰好是用其所长,而不是彰显所短。可见作者为文风格与文体演变之间,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元、白“新乐府”的创作,寅恪先生也从中国文体演变的角度给以特殊的解说。他写道:
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关于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详见《敦煌掇琐》及《鸣沙余韵》诸书所载,兹不备引。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钜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同上,第120~121页)
历来论元、白诗者多矣,从未见像寅恪先生这样把白氏新乐府和韩愈的以古文试作小说联系起来,从文体流变的角度厘定其创造性质,并将其创获置于陈子昂、李白改革齐梁文风的努力之上,而看作是唐代古文运动在诗歌创作领域的自然发展。文史学家虽不一定尽同此说,但元、白地下有知必以寅恪先生为隔世知音者矣。由此也可以理解,《元白诗笺证稿》为什么在《附论》章设专节“论元白诗之分类”,接着又专论“元和体诗”,对白居易说的“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白居易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503页)格外给予注意。因为论白诗者向以“老妪能解”来概括其特征,认为“元白诗专以易解之故,而得盛行”,寅恪先生于是辨体究元,给元、白之新诗体以高度评价。
尤可注意者,寅恪先生在论述文体特征和文体演变的时候,格外重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与助手僧睿探讨佛经翻译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西文的辞体,因而说道:“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梁]释慧皎撰《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第53页)鸠公提出的佛经翻译过程所遇到的这一华、梵文体相隔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土文士的注意,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文体演变的一大刺激。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以特别重视文体,实际上就与佛经翻译的影响有关(可参见笔者《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体流变》一文,载拙著《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28~45页)。毋宁说这也正是寅恪先生重视唐代的古文运动、重视元白文体革新的直接因由。所以他在《论韩愈》中申论说:“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惟仿偈颂音缀之有定数,勉强译为当时流行之五言诗,其他不遑顾及,故字数虽有一定,而平仄不调,音韵不叶,生吞活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读之作呕,此罗什所以叹恨也。”(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95页)虽不能说韩愈、元白等人的文体革新的尝试是沿续佛教翻译的特殊文体,但作为学理的参证,两者之间的异同关系殊值得注意。
《金明馆丛编初稿》
《论再生缘》和章回体小说
至于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寅恪先生则断定是由佛曲即演说经义的一种文学形式衍化而来。他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0页)罗振玉所刊《敦煌零拾》中有佛曲三种,第二种是《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如果以此篇与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的原文互勘,寅恪先生认为,可以发现演义小说这种文体的原始形式及嬗变流别的情形。按梵本《维摩诘经》本经,维摩诘居士本没有眷属,父母、妻子、子女均系抽象名词,所谓“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是也。但大藏经中却有《维摩诘子问经》一卷,似乎维摩诘居士又有子,而且《月上女经》更说维摩诘“有妻,名曰无垢”,生女为“月上”。这反映出此一佛经故事在印度本土已有滋乳演化的过程。译入中土之后,更“为之造作其祖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各系以事迹,实等于一姓之家传”,这与在印度本土的演变途径“不期而闇合”。对佛经文本的这种变化过程,寅恪先生比之为通行小说所写的杨家将之于历史上的杨氏,或者《说唐》《小英雄传》《小五义》以及《重梦后传》等“与其本书正传之比”(同上,第185页)。
他由此得一结论,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化早期曾有过佛教化的倾向。他说:“六朝维摩诘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假使后来作者,复递相仿效,其艺术得以随时代而改进,当更胜于昔人。此类改进之作品,自必有异于《感应传》、《冥报记》等滥俗文学。惜乎近世小说虽多,与此经有关系者,殊为罕见。”(同上)显然寅恪先生为演绎佛经故事的哲理小说在我国未获发达而感到遗憾。论者或云禅宗语录和元曲中的庞居士及其女灵照的故事,可以算作印度哲理化的中国作品,但寅恪先生认为内容摹似过甚,有生吞活剥之嫌,像用中国纺织品裁剪的布拉吉,终为识者所笑。那么,所以如此的原因究竟何在?寅恪先生用诘问的口气探讨这个问题,说道:
岂以支那民族素乏幽渺之思,净名故事纵盛行于一时,而陈义过高,终不适于民族普通心理所致耶?”(同上)
呵呵!寅老此处实际上提出了吾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问题。自晚清以还西潮冲击的结果,颇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有别,例如说中国是实际的,西方是论理的等等。他对时人之论未加可否,而是以一诘问句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近乎疑似之间。不过中国推理小说的不发达应是不争之事实,寅老所论相信世无异词。可见论小说文体的演变与民族的思维惯性联系起来,与受众的接受心理联系起来,是何等必要。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在1954年撰有《论再生缘》的大著,对一部鲜为人注意的讲唱文学作品给予令人震撼的评价,认为就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的特点而言,实不让于杜诗(陈寅恪论述弹词《再生缘》的文学成就,尝具引姚鼐和元稹对杜甫五言排律的极词赞美,然后写道:“弹词之文体即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故微之、惜抱论少陵五言排律者,亦可以取之以论弹词之文。”),而可以与印度、希腊及西洋史诗相提并论。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这样写道:
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之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陈寅恪:《论再生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1~72页)
这样来评价《再生缘》一书,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语,足可让古典文学及文化史研究者目瞪口呆。因为历来有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种文体。但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现在肯定地说,“吾国亦有此体”。不是别个,弹词体长篇小说《再生缘》就是。虽然西方的史诗在宗教和哲学方面自有义涵,但就文体而论,两者是相同的。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判断。
但人们不免还是要追问,寅恪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何以对讲唱文学如此感兴趣?《论再生缘》的开头有一段关于写作此书经过的自述,我们不妨细心体会。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同上,第1页)
很明显,寅恪先生写作此书的着眼点在于弹词七字唱这种文体。上引寅恪先生1930年撰写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一文,曾谈到佛曲的文体是“长行”与偈颂相间,衍变到后来,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便成为章回体小说,而“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0页)。更早一些的《有相夫人天生因缘曲跋》里面,也说过:“今观佛曲体裁,殆童受喻鬘论,即所谓马鸣大庄严经论之支流,近世弹词一体,或由是演义而成。”(陈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71页)
可见寅恪先生对弹词七字唱体的注意由来已久。甚至他在1953年听读《再生缘》的题诗中,也自称“论诗我亦弹词体”,尤表现出从文体上认同心情的迫切。因此亦不难理解《论再生缘》涉及对作品本身的评价,何以反复在文体特征上大做文章。盖此纯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加以立说。而且一如论韩愈、论元白长庆体诗,此处论弹词体长篇小说也是从作者思想的灵活自由和文体变化的关系着眼,提出《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七字唱体中所以孤芳独胜?是由于作者陈端生有非常自由活泼之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陈寅恪:《论再生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3页)。他并且追溯文章学的历史,指出“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同上,第72页)。六朝时期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和宋代汪彦章代皇太后所写的《隆佑太后诏书》,寅恪先生最为激赏,称前者为当时骈俪文的范本,后者为赵宋四六文之冠。
《哀江南赋》和《隆佑太后诏书》
寅恪先生对庾信的《哀江南赋》,写有专论,曰《读〈哀江南赋〉》,载于《金明馆丛稿初编》中。寅恪先生写道:“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於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这个评价,可是高得不得了。试想,“文章之绝诣”是何等遣词!
庾信的诗赋文章,自有其家学渊源。乃父庾肩吾,是梁太子的中庶子,为散骑常侍、中书令。当时徐摛为左卫率,摛子徐陵和庾信,俱以善属文著称,并为抄撰学士。徐陵是谁?就是《玉台新咏》的编撰者。《周书》庾信本传记载,徐陵与庾信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可知早年的庾信即以博学高才名动朝纲了。《周书》本传称,庾信容仪壮美,“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但是,当他四十二岁的时候,奉命出使西魏,他的故国首都江陵被西魏攻陷,他不得不羁留在西魏的都城长安。嗣后西魏又由北周所取代。西魏和北周的君主对庾信都是礼遇有加,曾先后授以重要官职。
历史的变化是富于戏剧性的,谁知北周和江左的陈后来又和好了。史载是一个叫毛喜的人,献陈周和好之策,使得南北悬隔的陈、周得以握手言欢。周的主理大臣宇文护拉着毛喜的手说:“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你看,还真的是握手言欢!陈周通好之后,南北流寓之士,很多都得以还其旧国。然而庾信却一再错过南归的机会。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写道:
二十年间陈、周通好,沈炯、王克、殷不害之徒,先后许归旧国。惟子山与子渊数辈为周朝历世君主所不遣放,亦不仅武帝一人欲羁留之也。今史文虽有差异,然于此可不置论。所应注意者,即此二十年间流寓关中之南士,屡有东归之事,而子山则屡失此机缘。不但其思归失望,哀怨因以益甚。
正是由于此种己身不能左右的社会政治背景,不情愿的阴差阳错的遭遇,长期念念于心挥之不去的家国之思,才使得《哀江南赋》这篇绝诣之作酝酿而成。为文者焉得不古事今情,混合古今;焉得不古典今典交互为用。寅老最欣赏的《哀江南赋》的结语:“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就是因为不仅用了李将军楚王子的古典,同时用了自己曾是“故左卫将军”的今典。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咏怀古迹》之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说的都是子山的《哀江南赋》啊!老杜可谓庾信的后世知音也。
至于被寅老称为赵宋四六之冠的《隆佑太后诏书》,我们不妨先看看《诏书》的原文:
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祲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祊,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宋]汪藻撰《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百五十六册卷三三六八,上海辞书出版社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
此篇诏书的撰著人为汪藻,字彦章,江西德兴人,南宋名臣,与胡伸一起,被称为“江左二宝”。《宋史》有传(参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三十七册,第13130~13132页),其所作四六文当时即已备受称誉,古今研究骈体之论著,无不将其置于君临之地位。因此寅恪先生称其为宋四六之“第一”,自不是虚美之词。耐人寻味的是寅恪先生所作的分析。他说:“此文篇幅虽不甚长,但内容包涵事理既多,而文气仍极通贯。又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但当日女真入汴,既悉数俘虏赵姓君主后妃宗室北去,舍此仅遗之废后外,别无他人可藉以发言,建立继统之君,维系人心,抵御外侮。情事如此,措辞极难,而彦章文中‘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两句,即足以尽情达旨。至于‘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古典今事比拟适切,固是佳句。然亦以语意较显,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职是之故,此文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陈寅恪:《论再生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2~73页)
能将颇束缚人的四六文体作到此种境界,寅恪先生认为归根结底是作者思想灵活自由的缘故,绝不是工于骈四俪六的一般人所写得出来。因此文体的解放,实际上是思想解放促成的,寅恪先生总结出了中国文体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论再生缘》的千古名句是:“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陈寅恪:《论再生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3页)至于此处之“世人”指谁,笔者愚陋,不敢枉自揣度。
虽然,寅恪先生对中国文体的有关论述,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多为片断,但在思想指归上却不乏系统性,而且不局限于文章学,更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待文体嬗变,从而使他的中国文体论成为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本文章版权归凤凰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